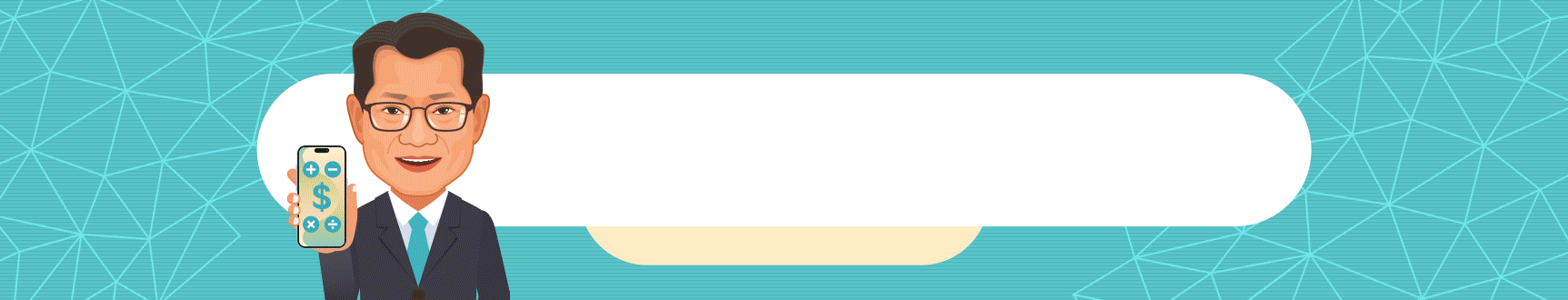香港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黃裕舜,2月24日在大公報《「一國兩制」實踐新階段筆談》專欄刊發文章《抓緊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開放的歷史機遇》,文章稱,應當把港澳本土文化、嶺南廣東文化進行保育,善用特區的獨有開放性,推動中外文化融合。政府應當鼓勵及資助破格創新的文化互動、實驗與交流,從而反映出中國獨有的多聲音、多樣性、內在多元特徵。
文章指出,「一國兩制」新階段的關鍵在於發展與開放,在穩守國家安全的基礎上,發展與開放乃「一國兩制」新階段的重中之重。
文章指出,高水平開放需要港澳海納百川、以世界的語言說好中國故事,港澳地區應善用與國際社會的現有來往,弘揚港澳內在所蘊含的核心價值、建構出文化戰略,提升中國在海外的軟實力,從而道出一個立體而動人的中國故事,把「一國兩制」作為國家治理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定位與國際友人分享。
文章最後強調,「一國兩制」的未來由實事求是者所譜寫,「一國兩制」並沒有時限,而是港澳特區長遠走下去的核心奠基石,須有力維護。
以下為評論文章詳細內容:
抓緊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開放的歷史機遇
黃裕舜
(香港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概括了繼續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把握好的四條規律性認識:一要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二要維護高水平安全、推動高質量發展;三要發揮獨特優勢、強化內聯外通;四要弘揚核心價值、促進包容和諧。
一、「一國兩制」新階段的關鍵在於發展與開放
安全就如氧氣,乃生存的基本。然而一座城市能否蓬勃向上,發揮自己應有的潛力,需要的是發展。無論是通過深化對「一國」的立體認知及行動維護,還是對社會穩定及有序規劃的捍衛,現階段的首要目的乃落實「高質量發展」,讓港澳地區的本地生產總值、市民生活水平、國際競爭力、生產力等關鍵指標有所提升。確立了國家安全基礎以後,管治者更須把大量精力與資源投放在思考經濟如何轉型、社會應當如何實現機會平等、治理應當怎樣符合結果、程序及觀感公義要求。這些乃關乎到一座城市、一個特區生命力的核心問題。
發展是一個量質兼備的動態過程。在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中,我們要衡量發展的話,大抵傾向於觀察平均居民收入水平(中位數)、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對外貿易及國內投資增長等「量」性指標的變化。然而,在如沿海大省、香港、澳門那般的發達地區,除了最基本對經濟增長、通貨膨脹等維持在合理水平的期望以外,發展的成功更取決於各種「質」性的量度,包括就業工種的多樣性、市民一生中社會往上流動的概率,以及反映貧富懸殊程度的堅尼系數。人類發展指數的組成部分中,不但包括人均國民總收入,也包括了教育程度及出生時預期壽命等與生產總值無必然掛鈎的組成部分。說得直白點,成熟經濟體發展的試金石,便是普遍民眾生活有沒有獲得感、幸福感,以及對前景能否感到希望、動力及憧憬。
「高質量發展」,除了是對那些只求短利、盲目增長崇拜觀的一記當頭棒喝,更是對管治者整體治理結構的一種心態要求。要顧及發展對環境保育的影響、也要顧及發展能否長期持續下去,經濟會否過度側重某些結構性衰落的行業、又或是與個別經濟體構成過多的依賴,從而釀成結構性風險,實事求是地把經濟大餅「做大、做優、做強」,相信乃中央對「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深切寄望。
若上述四條規律性認識的第一、二點乃關乎治理目標的重點藍圖,那第三、四點則為對於落實藍圖起到核心作用的建構方法。港澳作為國家對外開放窗口,也是國家與世界的重要連接點。內聯外通中的「內聯」要求的不只是我們與內地同胞開放,也是我們能為他們提供關鍵的增值作用,補充企業及商家在知識面、司法制度、行政服務的不足,從而促進內地企業及個人「併船出海」,在海外打造由華人與當地人有機合作的商業基地。「外通」則更需要港澳特區擔任國家整體「走出去」潮流的先鋒和弄潮兒,積極地與海外各國展開合作——尤其是特區本身具備長年緊密聯繫的優勢,能夠協助建立更深的相互認識,同時也需有效地吸引世界各地頂尖人才,以港澳為基地去貢獻大灣區以至於全國的建設。
從中可見,港澳從政、行政、議政者須充分珍惜及把握兩個特區與內地在政治體制、經濟模式、文化思緒層面上「必要的張力」(陳端洪教授用詞)。箇中所指的不限於港澳地區長年實行讓市場發揮關鍵作用的資本主義,與內地社會主義的制度性區別,也包括港澳地區與世界資訊、資金、人員相對於內地更為流通、港澳地區具備法定雙語特性等的重點區別。2022年,習近平主席視察香港時發表的重要講話,曾兩次提及「普通法制度」,這具體反映了香港有必要在普通法方面加深鑽研及與國際接軌,更積極地提升我們在普通法國家與地區的聲譽及法律聯繫。
當然,若要有效弘揚核心價值、同時維持社會和諧共處、百花齊放特色的話,我們絕不能「為開放而開放」,而是要有目的和戰略性地開放。開放絕不能把基本安全置於險地。比方說,港澳的戰略性基建與產業絕不能落入外國別有用心的資金手中。我們在引進外來資金時,也要提高相應的透明性與資料披露的要求,從而保障港澳同胞的廣泛福祉。而社會基本安穩與開放兩者之間並無根本衝突。我們固然不能把一切風險消除,但我們在開放過程中也得進行適度的風險管理。確立基本底線以後,推動開放方能更全面、更自在。
綜上所述,在穩守國家安全的基礎上,發展與開放乃「一國兩制」新階段的重中之重。面對地緣政治動盪,舊有發展模式動能不足而缺乏多元化、新發展模式仍處在醞釀的過程中,再加上保護主義、形式主義、政治渲染主義嚴重,以及社會上還有些人對於中央對港澳的期望依然存有認知偏差,如此種種皆不容我們輕描淡寫地忽略。唯有堅守發展與開放兩大方針,港澳方能再創輝煌,即使面對風高浪急的國際形勢,也能採取主動,捍衛港人澳人利益,也為國分憂。港澳地區高度自治權與中央全面管治權之間並不存有對立,而是通過時刻的辯證與平衡,從而達至全面而有效的統一。
二、高質量發展需要敢於破局、勇於嘗試的改革精神
讓數億人民脫貧致富、建設小康社會,以及中國在不同的多邊組織中起到重要作用、成為全球南北方之間的橋樑,從而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大國、重回世界舞台中央,這個過程當中的核心動能離不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所啟動的改革開放進程。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於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提出,「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從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
過去五年走來,中央對港澳發展的指導與敦促,皆出現了關鍵性的轉變。面對內外困難,港澳沒有不變的餘地,也沒有不推動制度性改革的空間。政制演變的軌跡中,每一個階段皆有偶然及必然的部分。偶然的是演變成為危機與沸點的「灰犀牛」及「黑天鵝」。必然的則是體制對其的回應。改革為偶然與必然互動下的產物,也是一個時期進行的動態過程,並無休止符。然而,改革方向乃取決於初心——在港澳層面這便是「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改革不能把「一國」基礎動搖,也不能讓「兩制」輪廓模糊化、區別變得渾濁。
那我們應當如何燃起改革精神,既不向作繭自縛的守舊者讓步、也不隨波逐流地向民粹主義低頭,從而創出經濟新氣象?
一,須積極深化「兩制」的優勢發展。廣納意見,兼聽則明,讓對現況有所誤解或質疑,甚至理性批判者能看到體制容納他們聲音的胸襟與決心,從而實現「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下的民心回歸,凝聚社會最大公約數。從政者無需凡事皆要中央提醒,應廣泛與各界商討與協調,在參考國家整體政策後制定反映改革決心的「十年發展願景」,從而向中央及港澳市民展示出應有的魄力。無論是普通法還是歐陸法,港澳兩個特區皆是中國土壤上最能與國際社會在司法層面接軌的先試區。行政立法機關皆需要尊重司法機關的程序公義,並積極從海外招聘更多尖端司法人才,鼓勵司法機關人才多到外地交流及解說實況,反駁失實指控。廉政公署是港澳班子清廉的壓艙之寶,須更鮮明賦權,肅清藏污納垢者。地區治理平台應該是為一般民眾提供去政治化且具備合適門檻的公民參與的機遇,從而鼓勵更多有心有力的政治素人青年人投身服務民眾的事業中。
二,港澳須尋覓新經濟增長引擎。此過程需要我們在宏觀層面上進行全方位規劃與廣泛協商、在微觀操作層面上保存靈活彈性,充分「留白」民間與商界領袖去進行想像及規劃。港澳制度獨特性的根基,在於其由下至上的有機政策制定程序、對民營企業在不少商業領域當家作主的鼓勵,以及對資本市場邏輯的尊重與信任。
更具體來說,香港可考慮以高等教育為核心基礎、大規模引入世界頂尖師資、海內外一流院校到香港設置分校,以吸引不只內地,也能包括歐英美、亞非拉、日韓等地的尖子來港就讀高等學府。修畢本科、碩士或博士而具上進心的人才,我們應當留住他們在港發展,積極推動香港在發展產業鏈上游調研、拓展中游專業服務增值、實現整體管理產業程序數碼化及監管科技去中心化等方面的嶄新發展。唯有完善的事業晉升階梯,方能吸納具雄心壯志者到港落地生根。
同時,香港也要積極研究如何利用金融工具與創新為本地基建、大灣區高端科技產業發展提供底氣,從而讓金融此湧泉孕育出我們在航運及貿易方面的戰略性突破。正如有建議認為,香港可考慮降低優質內地國際企業在港上市門檻、強化內地和香港監管協調,以香港作為金融監管先行先試地,去除不必要的架床疊屋,也要同時確保監管架構與時並進,能堵塞過大的系統性風險。長遠而言,香港應把自身設定為亞太地區各國(尤其是東盟與中亞)企業第一及第二上市的首選之地,也要探索以離岸人民幣作為各地政府發債及融資工具,以金融渠道連接內地與世界。正如正在積極探究博彩業以外經濟支柱的澳門,香港應當更精準地推動經濟適當多元發展,在地提升教育制度對國際外向視野及與科技共存共處能力的栽培。
三、高水平開放需要港澳海納百川、以世界的語言說好中國故事
未來二十年,香港應朝着一千萬人口的目標出發、優化從世界各地吸納人力資源、金融資本、新興構思與概念的程序。然而究竟外國資金、人才、創新發展者,為何要來香港而非紐約或倫敦、上海或新加坡發展?對旅遊觀光感興趣的,為何他們要來港澳,而非內地諸多的美麗城市?
事實上,港澳對國際社會的獨特魅力,在於我們接納來自於五湖四海人才的胸襟及空間。促進高水平開放,須海納百川,確保社會主流中的價值觀及意識形態百家爭鳴,和而不同。比方說,司法制度上,除了要與國際社會(尤其是發達地區)進一步接軌,也可有秩序及知性地把國際規範、體系、法律推薦到內地,同時把中國對新興科技的治理思想以國際話語及格式輸出,糅合東西南北各方所長,推動中國與世界在知識產權法、人工智能法、科技監管法等層面的銜接。國家具制度自信,而港澳在這方面應有足夠的創新自信,去推陳出新、青出於藍。
一,要深度對接國家戰略,需要港澳反思自身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有何無法取代的獨特作用。相對於內地,港澳的輿論空間更為開闊、數據更為開放、與英語葡語世界的文化及人文聯繫更為豐富、也更容易吸納對中國存有不足認知的外國友人到訪。港澳因此能作為「出海」的先頭部隊,善用港商澳商在海外經商的網絡與知識,充當有意進入中國市場的海外企業的橋樑,為內地企業引領路徑、搭橋鋪路。
港澳也能在民間外交上起到指標性作用,讓對中國缺乏認識、信任及接觸的朋友與內地體制內外聲音交流,以「二軌對話」破除國與國之間所樹立的高牆堤壩,方能為國家構建新發展格局。固然港澳地區須提升當地從政者、商界及民間對「全球南方」的認知,鞏固與東盟、東歐、中東、拉丁美洲、非洲等新興經濟體的合作基礎;而國家也需要澳門與葡語世界加深就着旅遊、娛樂、教育、歷史保育的協作互動。同時,作為遊走於「全球北方」中的和平「使者」,香港必須維持與西方國家、日韓等發達經濟體的關係熱度——正因如此,香港更要向這些國家民間中對中國抱有興趣者招手,對質疑聲音作出直接坦率的回應,對無知者伸出橄欖枝,積極深化與他們的接觸交流,絕不能把大門關上。
二,港澳地區應善用與國際社會的現有來往,弘揚港澳內在所蘊含的核心價值、建構出文化戰略,提升中國在海外的軟實力,從而道出一個立體而動人的中國故事,把「一國兩制」作為國家治理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定位與國際友人分享。港澳居民當中很多少數族裔居民(包括印度裔、葡萄牙裔、猶太裔、日韓裔等)生於斯,長於斯,對港澳擁有強烈的歸屬感。他們也是正宗的香港人、澳門人。對外,他們能成為特區最佳的「國際使者」,與海內外的族裔僑民建立聯繫,並以真摯而地道話語,而非過多修飾的套話,說出他們心目中的「港澳故事」。對內,我們應當把港澳本土文化、嶺南廣東文化保育,善用特區的獨有開放性,推動中外文化融合。在香港,《杜蘭朵》也可跟《帝女花》結合、崑曲與芭蕾舞也可糅合,作為藝術創新的典範。在澳門,經在地化後,傳統葡萄牙菜演變成具印度和馬來西亞半島及華人文化特色的澳門土生葡菜。政府應當鼓勵及資助破格創新的中心文化互動、實驗與交流,從而反映出中國獨有的多聲音、多樣性、內在多元特徵。
四、「一國兩制」的未來乃由實事求是者所譜寫
2022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香港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清晰強調,「一國兩制」「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一國兩制」並沒有時限,而是港澳特區長遠走下去的核心奠基石,須有力維護。只要我們大家穩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間鮮明而有機的區別,堅拒內捲的形式主義、一成不變的官僚主義、停滯不前的本位主義,抓緊發展機遇與把握開放空間,相信香港、澳門未來必然能再創輝煌!
(來源:大公報)
更多閱讀: